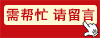杀头潲猪等过年
很多年前,在湘南农村,种田和养猪几乎是每家每户的通用模式,搞“大集体”后期即已流行,土地承包经营到户后又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,只是后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和农村建房用地的需要,荒废的猪舍慢慢都被拆除了,特别是随着人们对环境卫生认识水平的提高,农户散养的现象基本绝迹,搞集中养殖的大户倒是涌现了不少。
那个时候,家家户户都会养上一两头猪,既为了以备不时之需,譬如遇到家人有三病两痛的、小孩读书要用钱的,把猪卖了就能凑几个钱、帮上一点忙。更重要的,是到了过年的时候有年猪杀,这可是脸上有光的大事,非同小可。记得父母那时候就爱念叨,有钱冒钱,杀猪过年,若是过年前没杀猪,他们会觉得在左邻右舍中抬不起头的。
一般来说,农户养猪都是每年4、5月左右买进小猪崽,喂到年底差不多就可以出栏了,是卖活猪亦或是杀猪卖肉,这就要视各家情形而定了。当然也有当年不作处理、要等到第二年开春后杀猪卖肉的人家,这样的人家不外乎两种情形,一是养的猪多,杀了年猪,栏舍里还有;二是特别精明,过年的时候杀猪,大家都赶趟,肉多价贱,卖不上好价钱,第二年开春后正是青黄不接之时,猪肉肯定好卖。
养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圈养的家猪,只有两项活动:吃了睡,睡了吃,对猪食的需求量特别大。那时候还没有专门的喂猪饲料一说,曾在湖南红极一时的“正虹”牌猪饲料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事,至于后来电视上“饲料霸屏”的局面还远远没有出现。当时农户家养猪,主要吃谷糠、青菜、酒糟之类,还有家庭里一日三餐的剩饭剩菜,这些还不够,就得安排家人时不时外出打猪草。吃这类东西长大的猪,农村俗称为“潲猪”,潲猪肉肥瘦适中,肉质紧实,鲜美可口,天然无公害,时至今日,仍是人们的追捧所在。
我的父母做田里的活都是好手,但养猪一事却不是他俩的强项,一样的喂养,一样的操持,但三天两头要请兽医过来,到年底的时候,邻居在隔壁栏舍养的猪膘肥体壮,我家栏舍的猪明显要小一号、小几号。有一年,气得父母从邻近村请来了一个“法师”,又是焚香,又是烧纸的,末了还往栏舍里扔了几挂鞭炮,把两头猪炸得嗷嗷直叫,但那年养的猪仍旧长得不咋的。
猪不长,家里人要多受不少罪。父母操劳自不用说,连带我和姐姐也要比别人家的孩子辛苦些。那个年代,人吃的粮食尚且勉勉强强,吃剩下的自然不多,父母便在自留地上多种了一些菜,而我和姐姐的任务则是每天早上一篮猪草。
我的老家在衡东县大浦镇三才村,屋门前有一条叫“堰子”的小河,发源于德圳冲里,自南向北流入霞流镇的“白衣港”后汇入湘江。横亘小河的是一座解放前就有的小石桥,叫曾家桥,往上依次有阳门桥、黄屋桥和S336线飞跃桥,往下是平田桥和京广线铁路桥,从飞跃桥到铁路桥七八公里长的河段,都是沿岸农家喂猪打草的范围。那时候,河水清澈,水草丰满,尤其是河里长着一种叫做“扁担草”的水草,是打草人的最爱,丛丛簇簇,蓊郁葱茏,跳到水中小范围抓扯,就可以完成大人们安排的一天任务。至于两岸的土坡上,还生长着紫花苜蓿、苦荬菜、鱼腥草、马齿苋、灰灰菜、蒲公英等野草,都是可以用来煮熟做猪食的。
少年的我们,寻猪草的最爱线路,是顺着小河往铁路桥方向走,不仅是越往下走水面越宽、水草越多,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——可以近距离看火车。那时候京广铁路线上电力机车已经很普遍了,但货运列车还大都使用蒸汽内燃机作动力,经过铁路桥时,火车司机远远的就会拉响汽笛,一声声呜鸣响彻云霄,钢铁巨兽急速驶来的压迫感扣人心弦,伴随车轮与铁轨碰撞产生的“哐当哐当”声,仿佛大地都在颤抖。列车挂载很长,几十节车厢,人站在一个地方不动,感觉一辆列车要全部经过完,需要好几分钟时间,在这几分钟里,人会感到非常渺小,有种风驰电掣、泰山压顶、呼吸急促的感觉。遇到绿皮火车通过,胆子大的伙伴还敢朝车窗背后的乘客做上一个鬼脸,或者是大声吼叫几下,并使劲挥动小手臂,以示自己的友好与勇敢。
暑往寒来,一年的辛苦忙碌,最终是看宰杀年猪。冬至一到,就进入了宰杀旺季。经常到我们组进行宰杀活动的,是本村一位姓綦的屠户。綦屠户中等身材,40多岁的样子,长相英俊,谈吐文雅,若不是穿在身上的一条围兜油光发亮,根本看不出他做着“白刀子进,红刀子出”的营生。
杀猪那天,是我们一家既紧张又幸福的时刻。大约凌晨二三钟的时候,事先接到通知的七大姑八大姨们陆续赶了回来,大家聚在堂屋里烤着火,一边诉说着家长里短,一边在等候綦屠户的到来。4点钟左右,綦屠户会如约而至。大家纷纷散开帮忙,掌灯的,帮忙捉猪的,烧水做饭的,照看小孩的,忙而不乱,轻车熟路。綦屠户不慌不忙穿上他的标志性围兜,在众人的帮助下把拼命挣扎的“二师兄”按在用四条长凳拼做的操作台上,对准咽喉处快速一刀,一股水柱状的鲜红随即喷薄而出,直泻到事先准备好的木盆里。之后便是“小猪变大猪”、“开水烫死猪”、“内外科手术”等环节。最让我惊奇的是“小猪变大猪”节目,綦屠户用刀将猪的四蹄皮肉处各挑开一个口子,用一根铁质通条从口子插入猪体各个部位,然后对着口子使劲吹气,不一会的功夫,猪的各处便鼓胀起来,全身找不到一处褶皱。据说,这样做是方便后面的褪毛工序,而且肉质会更加鲜嫩。
最后是猪肉处理环节。有的年份,亲朋戚友可以将一头猪包括内脏、排骨、龙骨、猪脚等全部买走,有的年份,大家选购之后还有剩余的,父亲就会请綦屠户带到附近集市上去卖,这样做,家里会立马有现金进帐,而亲戚买去的,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钱付。
当然,杀年猪的当天早餐,毫无疑问是一次亲朋戚友大会餐,新鲜的猪血丸子汤,嫩炒猪干,红萝卜焖肺片,还有干辣椒炒大肠,这几样都是母亲的绝活。辛苦一年,一场忙碌,家里留下的不过二三斤肉和一个待处理的猪头,而这,十有八九就是我家过年的硬菜了。
一晃,几十年过去了,我家早已不再养猪,更不会宰杀年猪了。我问父母,那时忙忙碌碌为了什么。年近九旬的父母亲顿了顿,然后字斟句酌地开口道,我们那是在过日子。我沉默了,也许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,珍惜当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