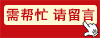菊 骨
秋意漫过电影湖畔时,岸芷渐枯,芦荻飞白,唯有篱边丛菊,攒着细碎的金,在风里轻轻颤。指尖抚过刘亚乘先生的墨迹,"陶之爱菊""予独爱菊"的字眼洇着墨香,混着菊的清苦气,竟像穿越了千年的风,吹得人心里泛起一层细浪。
古人说花,总爱论个高低。牡丹是天家富贵,开时轰轰烈烈,层层叠叠的瓣裹着胭脂气,惹得长安仕女簪满头,连帝王都要为它挪动花期,那份"妖"与"贵",是活在万众瞩目的光晕里。莲花却不同,生在污泥里,叶擎着水,瓣托着露,周敦颐说它"濯清涟而不妖",是把高洁刻进了骨里,站在水中央,自带三分疏离的傲气,像前朝的隐士,不肯与俗世同流。
可菊呢?它从不是争春的主儿。春有桃李争妍,夏有荷风送香,到了秋深露重,百花敛了锋芒,它才肯从篱边、石缝里钻出来。不挑水土,不择贵贱,田埂上能长,庭院里也能活,枝干是瘦硬的,像文人笔下的瘦金体,没有半分谄媚的弯;花瓣是细碎的,拢着黄蕊,不似牡丹的浓艳,也不及莲花的清丽,却自有一种清直——风来不折腰,霜打不垂头,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开着,把秋的萧瑟,都染出几分暖意。
陶渊明爱菊,大概是爱它这股子"隐"气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,见着篱边丛菊,定是觉出了同气相求。你看它不往闹市去,偏守着田畴篱落,像个沉默的知己,陪他种豆南山,陪他戴月荷锄。花开了,采一把插在陶瓶里,浊酒一杯,诗一首,日子清苦,却活得坦坦荡荡。这菊,哪里是花?分明是他不肯向俗世低头的骨。
周敦颐说"莲,花之君子者也",可莲的君子气,带着几分孤高,让人敬而远之。菊的君子气,却藏在烟火里。它能入茶,沸水里滚过,涩中带甘,像把秋的清冽喝进了肚里;能入药,和着甘草、蜂蜜,治得了肺热,也解得了心燥; even落在寻常百姓家的窗台,不用精心伺候,给点阳光雨露,就能开得热热闹闹,不端半点架子。
电影湖畔的菊,该是得了这湖光的浸润。水边的丛菊,叶上总挂着露珠,风过时,露珠子滚进湖里,漾起细微波纹,倒像是菊在和湖水说悄悄话。刘亚乘先生的字就刻在旁边的石上,"清直""净植"的字眼,和菊的影子叠在一处,倒让人想起那些守着初心的人——不必做牡丹的富贵,不必学莲花的孤高,只在自己的方寸里,活得清清爽爽,直来直去,像菊一样,把根扎在土里,把花向着光,不与谁争,也不向谁屈。
暮色渐浓时,风里的菊香更清了。远处的灯亮起来,映着湖面的碎金,也映着篱边的菊。忽然懂了古人爱菊的痴——它哪是爱一朵花?是爱那花里藏着的气:不媚俗的骨,不清高的温,在烟火里扎根,在风霜里绽放,活得像自己,就够了。
就像这湖畔的菊,就像写菊的人,就像每个在平凡里守着清直的我们。(作者:曹姣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