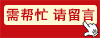甘建华||寻访抗战老兵陈诗祥
栗江水在冬阳下泛着淡金波纹,像被岁月揉皱的铜箔,贴着茅洞桥(今茅市镇)的田埂缓缓流淌。我站在观音堂往镇上去的路口,望着河面上掠过的野鹜,忽然想起幼时听乡老讲的“抓特务”故事——那些藏在稻草垛后的暗哨、月光下摸进圩场的黑影,原以为是说书人编造的传奇,直到冒着2018年11月的冷雨,走进陈诗祥老人的家里,才惊觉所有惊心动魄的情节,都曾在湘南山中这片红土地上真实发生过。

这年深秋已经连下两旬雨水,云层低得能蘸湿檐角的枯草,淡墨似的云絮压在山尖上,把整片田野都浸得发潮。我们驱车前往清逸村陈诗祥家,狭窄的水泥公路在山间蛇行,路旁的小河漂浮着残败的枯叶,电线上落着成群麻雀,黑黢黢的一片,像是谁随手撒在半空的炉灰。同行的派出所所长说在茅市工作十七八年,竟然不知有这么一位抗战老兵。村干部都认得陈诗祥,却只当他是村口晒太阳的普通老者。就像田埂上的苦楝树、墙角的青苔,他早已和村庄的肌理长在一起,寻常到无人留意他年轮里藏着的烽火岁月。

陈诗祥家的堂屋朝着栗江,木窗棂上糊着旧报纸,风一吹就簌簌响。老人已经提前得知来客的消息,我们进门时看到,他正从床头的衣堆里摸出一件军装,灰绿色的布料泛着旧光,左胸佩着两枚勋章,一枚是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”纪念章,另一枚是后来补发的“抗战老兵”荣誉章。他没有理会我们“天冷别换衣”的劝阻,枯瘦的手指捏着衣扣,颤巍巍地解着家居棉衣的纽扣,动作慢得像在拆解一段尘封的往事。孙子陈金龙说爷爷耳背,可那刻老人的神情却异常专注,仿佛眼前不是一件旧军装,而是当年别在腰间的手枪,或者背上的冲锋枪。
待他把军装穿妥,再把军帽轻轻扣在稀疏的白发上,整个人忽然变了模样。原本佝偻的背尽力往前挺,浑浊的眼睛里竟透出些光,像蒙尘的枪膛突然被擦亮。他拄着一根拐杖,慢腾腾走向堂屋的木沙发,坐下时腰板绷得笔直,双手放在膝盖上,指关节突出得像老树根。那双手曾握过钢枪、埋过炸药、押过俘虏,如今却连端碗都要借助外力,可掌心的老茧、指节上的疤痕,仍能看出当年的力道。我盯着他的面庞看了一会儿,额骨、眼眶骨、鼻骨、颧骨都清晰可辨,像是被岁月反复打磨的青石,唯有那双眼睛,像深坳中的潭水,藏着太多沉底的故事。
“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(1924年9月19日),我出生在茅洞桥王书坳。”陈老的声音很响亮,堂屋门口的黄狗都被惊得抬了抬头。他说自己是兄弟五个里的老满,3岁没了爹,13岁没了娘,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湘南农村,“能不饿死就是福气”。16岁那年,他跟着老乡陈志统去广西桂林谋生,介绍人王连英是部队副官,给了他一份勤务兵的活计,在民政情报指导处做事。后来他才知道,这个指导处归军统保密局管,下辖两个科和一个密查组,他被分在二科,办公室在蒋介石行营和军政部之间。

“那时我太年轻,啥也不懂,提着热水壶跟蒋先生擦肩而过,也只当他是个普通长官。我只认得前后两任科长,第一个叫吴易文,后来那个叫杨风伟。我知道他们是我的长官,我的命攥在他们的手里,所以,我对他们毕恭毕敬。”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,仿佛在说昨天赶集遇到的邻人,可我却能想象得出当年的场景。再不用饿肚子的少年,穿着一身粗布军装,目不斜视地穿过走廊,皮鞋踩在水磨石地上的声响,混合着办公室里的电报声、谈话声,成了他青春岁月最特别的背景音。
1940年的桂林,已是抗战的前沿阵地。日寇飞机时常从上空掠过,炸弹落在漓江上,水花能溅到行营窗台上。陈诗祥说自己只训练了一个月,就从勤务兵变成正式军人,与另外14个年轻人组成别动队,住在柳州湖南会馆,受军统保密局指挥。“我们穿着便装,腰别手枪,白天在街上游逛,夜晚摸黑去炸军火库。”说起有一次去全州抓特务的经历,他的眼睛亮了起来。那天他们拿着保密局的介绍信,找到全州自卫队队长赖旭忠,白天装作赶集人,摸清了日本特务的住处。等到月黑风高,几个人翻墙进去,没费多少劲,就活捉了两个特务,其中一个挣扎时被失手打死,另一个交给了自卫队。“那时不怕死,就怕任务完不成。”他说这话时,下颌骨在两耳前上下跳荡,就像在踩踏老式打谷机。“国家都要没了,命还算个啥?”想了想,他又补充一句。
最让他难忘的是全州黄沙河战役。部队配的是美式冲锋枪,每挺18斤重,带50发子弹。他背着枪,在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,“怕掉队,就跟着前面人的脚步声。”任务是炸黄沙河大桥,阻止日军过河。那天夜里,没有月亮,河面黑沉沉的,只有桥头几盏油灯亮着,像鬼火一样闪烁。他和两个战友摸向桥头,趁哨兵不注意,一把捂住对方的嘴,反剪了胳膊就往回带。“敌人发现后,我的右腿中了一枪,血顺着裤管流,却也顾不上疼痛。”待他们把俘虏押回驻地,身后的大桥已经炸响,火光映红了半边天。美国援华飞虎队的飞机在天上盘旋,有一架被流弹击中,飞行员跳伞落在山里。
“整整三天三夜,我们在山里寻找那个美国兵。”陈诗祥讲到这里,停了下来,眼睛望着门外的青山,像是在寻找当年的踪迹。他说那三天没怎么吃东西,全靠野果和溪水充饥。最后在一个山洞里,他们找到了飞行员,人受了点伤,却还能走。“把他送到全州自卫队时,他拉着我的手,用中文说‘谢谢’。”老人模仿着当时的动作,枯瘦的手在空中比画,“那时才晓得,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在打鬼子,还有全世界都在帮我们。”
可战争的残酷远不止这些。他说别动队15个人,有3个死在炸桥的任务里,还有两个在后来的游击战中失踪。“1945年上半年的一天,我们完成任务回来,部队已经转移了,彻底失去联系,我们成了没人管的兵。”说到这里,他的声音低了下去:“我不想再打仗了,只想回家,就一路讨饭往衡阳方向走,走了半个多月,才到茅洞桥。”家乡的稻田还是老样子,栗江水还在流,可他却觉得自己像个外人。身上的军装早已换成破烂的百姓服,枪也扔了,只有腿上的伤疤提醒着他曾是一个军人。
1952年,陈诗祥搬离王书坳老宅,在堂客娘家长沙塘(后合并到清逸村)起房子安家,生下三男二女。桂林的当兵岁月、别动队的生死经历、枪林弹雨的日子,他从没跟家人提起过,就像用灶灰埋了火种,生怕一不小心就会烧起来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有人对他在外的经历产生怀疑,将他抓进大队部,关押吊打三天三夜。“他们问我是不是军统特工,我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坏事,其他事情一概不知道。”他说那时最害怕的,是遇到当年的战友。茅洞桥大概有五六个和他一起参军的人,可每次在街上见面,互相都只能假装不认识,得赶紧将眼睛闪开。他说:“我怕连累对方,也怕自己再被揪出来,那样就会被活埋。”直到早些年,那些战友都走了,他才敢跟二女婿聊起一点陈年旧事。
命运的彻底改变发生在2015年9月3日。那天,二女婿在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广场阅兵式,看到抗战老兵被颁发纪念章,其中包括曾在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战、后来回乡务农的老战士。女婿赶紧跑到他家,喜孜孜地说:“爹,国家认你了!”陈诗祥盯着电视里的画面,眼泪突然间奔涌而出,那些被他埋在心底里几十年的伤痛,那些不敢言说的委屈,终于有了一个正名。
这一年,陈诗祥91岁,第一次领到国家5000元一次性补助。嗣后每月有500元生活费,逢年过节有慰问品和慰问金。拿到纪念章那天,他把奖章别在胸前,在门前禾坪上走了好几圈,还哼起了当年部队里的“兄弟歌”:“团结就是力量,团结就是力量,这力量是铁,这力量是钢……”
2018年那次采访后,我再没见过陈诗祥老人。听他的孙子告诉我,2021年夏天,他已经卧床不起,却还时常把军装穿在身上,嘴里喃喃地说着“黄沙河”“美国兵”。同年9月6日,离他98岁生日只差13天,老人因病遽归道山,走时身上盖着那套军装,两枚勋章放在枕边。
如今再去茅洞桥,栗江水还在流,陈诗祥家的堂屋换了新窗棂,可木沙发还在原来的位置,仿佛还坐着那个穿军装的老人。村里人说,每年清明节前后,都会有年轻人来打听陈诗祥的故事,有人还带着鲜花,放在他家门口的老槐树下。像陈诗祥这样的抗战老兵,是“历史的活化石”,他们的经历,藏着一个民族的抗争史,也藏着国家对历史的尊重——从“军统特工”到“抗战老兵”,这不仅是一个身份的转变,更是一个国家对过往的正视,对每一个为民族牺牲的生命的敬畏。
又是9月3日,北京正在举办世界瞩目的大阅兵。我又来到茅洞桥,伫立栗江岸边,望着河水流向远方,汇入大河湘江。远处的稻田里,收割机在收割晚稻,金黄的稻穗被卷入机器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忽然想起陈诗祥唱的“兄弟歌”,想起他说的“中国永不亡”,想起那些在硝烟中出没的前辈、那些为抗战牺牲的人们。原来,我们今天脚下的每一寸土地,都曾被他们的鲜血浇灌;我们今天享受的每一份安宁,都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。而像陈诗祥这样的老兵,就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,他们把历史的火种传递给我们,让我们永远记得: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不过是有人曾为我们负重前行。
风又吹过栗江,水面泛起涟漪,像在诉说着永不褪色的记忆。我对着陈诗祥家的方向,深深地鞠了一躬——敬这位抗战老兵,敬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,更敬懂得铭记历史、尊重英雄的国家。
甘建华,生于1963年8月18日,湖南衡阳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,中国散文学会理事,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第二届副会长,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,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客座教授,南华大学衡湘文化研究所研究员,衡阳师范学院终身客座教授,衡阳日报社退休高级编辑。出版文学、新闻专著及配套评论集三十余部,主编中国文化地理诗文选本多部并有理论建树,作品入选海内外上百个权威选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