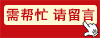耒水夜泊:水波里的星月与乡愁
暮春的傍晚,我乘一叶小舟泊在耒水中央。桨声渐歇时,暮色已漫过两岸的芦苇,将整片水域染成温润的墨色。船家往舱里添了把柴火,陶罐里的米香混着水汽飘出来,恍惚间竟与儿时外婆在耒水畔煮的粥香重叠——这便是故乡的水,连风里都裹着化不开的牵绊。
船身轻轻晃着,像躺在母亲的臂弯里。抬头时,一轮圆月已从东洲岛的树梢爬上来,清辉洒在水面,碎成满河的星子。伸手去触,指尖只碰到微凉的水波,那光影却在掌心晃啊晃,忽然想起《古文观止》里《赤壁赋》的句子:“月出于东山之上,徘徊于斗牛之间。白露横江,水光接天。” 苏子当年夜游赤壁,见的是长江浩荡,而我眼前的耒水,虽无大江奔涌的壮阔,却有小家碧玉般的温婉,连月色都似多了几分柔情。
远处的渔火亮了,一点两点,散在朦胧的夜色里。渔翁撑着竹篙缓缓划过,船尾的涟漪推开月影,又很快被新的水波抚平。他嘴里哼着耒阳小调,调子软软的,混着水流声,竟比城里的音乐会更动人。想起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里写 “渔歌互答,此乐何极”,当年他登楼见洞庭盛景,叹的是 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 的家国情怀;而此刻我听耒水渔歌,心头漾开的,却是最朴素的乡愁——是儿时跟着外公在河边网鱼,他教我辨认水草与鱼虾的模样;是外婆在码头上唤我回家吃饭,声音被风送得很远;是夏夜躺在竹床上,听大人们讲蔡伦造纸的故事,看流星坠进耒水的微光。
船家递来一碗热粥,白瓷碗贴着掌心,暖意顺着指尖漫到心里。粥里加了耒水畔特有的芡实,软糯清甜,还是记忆里的味道。他说:“这耒水啊,养活了咱们耒阳人几代。以前没桥的时候,全靠渡船来往,夜里的船最多,都是赶早去城里卖菜的乡亲。” 我望着岸边的灯火,想象着从前的夜晚:满河的船儿载着新鲜的蔬菜、刚织好的布,桨声、笑声、叫卖声混在一起,是耒水最热闹的烟火气。如今桥多了,渡船少了,但耒水依旧日夜流淌,像一位沉默的老者,守着故乡的岁月变迁。
风渐起,吹得芦苇沙沙响。月光下,对岸的蔡伦竹海隐约可见,墨绿的轮廓像一幅淡墨山水画。想起《赤壁赋》里苏子与客泛舟,叹 “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”,而耒水虽短,却也流淌了千年。它见过蔡伦造纸时的草木青烟,听过杜甫泊舟时的沉吟,也见证了故乡从泥泞小路到高楼林立的蜕变。河水会变,两岸的风景会变,但刻在耒阳人骨子里的乡愁不会变——是对这片山水的眷恋,对故土人情的牵挂,对简单生活的珍视。
夜深了,渔火渐次熄灭,只剩星月与船灯在水波里相依。我裹紧衣衫,望着眼前的耒水,忽然明白:所谓乡愁,从来不是抽象的思念,而是具体的、可触可感的记忆——是耒水的清甜,是月色的温柔,是渔歌的婉转,是粥里的芡实香。就像苏子在赤壁见山水而悟人生,范仲淹登岳阳楼而怀天下,我在耒水夜泊,见的是故乡的模样,念的是心底的归处。
舟楫轻摇,水波荡漾,星月的影子在水里晃了又晃。我知道,明日晨光熹微时,我将离岸而去,但这耒水的夜、这水波里的星月与乡愁,会永远留在心底,成为我无论走多远,都能回望的港湾。